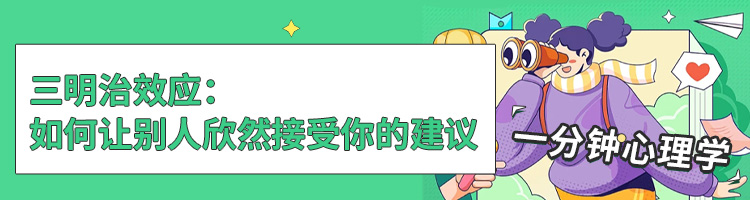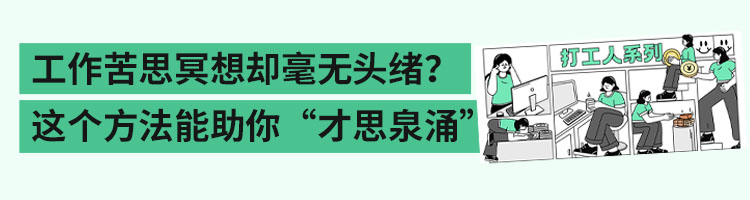“ 佛系青年”的时代病
“ 佛系青年”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病人,但确实患上了流行 的“ 时代病”。并且这一病症并非完全是新生事物,而是伴随着都市现代性发生发展。以精神分析的眼光观之,这是一种“负性幻觉”,它与消费社会的欲望生产机制密切相关。
“厌世”:都市现代性一副面孔
齐美尔在都市社会形成时期便敏锐地观察到了都市人的冷漠厌世特质,《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中他将“厌世”作为都市人的精神症候。齐美尔试图回答为何城市是厌世态度的真正场所。正是人、物、货币集中的刺激,制造了神经系统最高度的巅峰,引发了自我保全的反应,最终不可避免地将自我的个性拖向毫无价值的感觉,一种自我退隐的冲动。
无论“丧文化”还是“佛系青年”都以消极厌世为主要特征,尽管“丧”似乎比“佛系”更决绝一些。譬 如“丧”什么都不想干,而“佛系”该工作时工作,只是别指望我努力“;丧”不谈恋爱,而“佛系”该恋爱时恋爱,只是不吵不闹不作,对待对方更像是一名长期饭友,但事实上他们分享共同的价值观“:太多选择,我选择不选择。“”不选择”正是都市物质繁荣的餍足体验,与之对照,乡村的“冰花男孩”却是“没有选择”,因此齐美尔方说只有大都会的孩子才会显现出厌世态度。
“厌世”无疑是现代性的一副面孔。尽管卡尔内斯库提到了现代性的五副面孔没有“厌世”,但无论是审美现代性、先锋派、颓废、媚俗、后现代主义处处都与厌世相关,与齐美尔对于都市现代性的总结相互映照。譬如审美现代性强调厌恶中产阶级价值,并通过极其多样的手段来表达这种厌恶。先锋派是现世的反对者,有意识投身于传统形式的“自然”衰朽,竭力强化一切现有的颓败与衰竭症状。颓废则是“大繁荣”中的厌倦,是一种心理、道德和美学的自我欺骗,正如尼采所说,虚弱成为一种目标。至于媚俗艺术和后现代主义都是对现代日常生活的逃避,它围绕模仿和伪装,制造出欺骗与自我欺骗的美学幻觉。
这一弥漫着颓废厌世情绪的时代病也被称为“英国病”。但 1970 年代以来的“英国病”与以往不同,它与战后经济繁荣和高福利政策有关。其中有三个代表性的表现心态:其一,英国式。高福利导致社会失去朝气活力,基础产业的国有化导致国家失去竞争力,成为“日落帝国”,年轻人只能远赴美国一展抱负。其二,瑞典式。瑞典年轻人的典型口号就是“即使没钱也有好生活”“小国国民再怎么努力也没用”,他们认为日本人“过得太辛苦”,“不想成为这样的国家”。其三,日本式。经历了奋发进取的“团块世代”,当代日本年轻人似乎落入“穷充世代”,即“贫穷却充实也无妨”。大前研一指出,“穷充”的本质是“低欲望社会”,比英国式和瑞典式的高福利“穷充”有更深刻的隐患。日本式的“ 穷充”是因为1990—2000 年的泡沫破灭,造成经济停滞,不管多么努力都难以升迁,加薪无望。年轻世代“丧失物欲和成功欲”,追求“极俭生活”,社会充满“草食化”的青年“,穷充”的本质是“穷忙”。
“佛系”的价值观是对现代性诸面孔的剽窃和挪用,流行于日本,是“低欲望社会”的一个表征。然而“佛系青年”在当下中国的流行也具有中国特色。“佛系”一词来源于“佛系追星”,他们逆反流行的粉丝文化,以心如止水、“爱与和平”拒绝文化工业的绑架。与英日青年一样,面对这一代消费社会制造的“大繁荣”,他们以“极简主义”“禁欲系”退回自我的心灵乌托邦,表现出不愿意背负风险、辛苦工作的父母沦为负面教材、“微高价”消费、小确幸、“选择不拥有”等心态。但是,与北欧高福利体系不同的是,“佛系”中国青年的逃避并不能逃脱户籍、房价、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的巨大现实压力,“穷充”只是“穷忙”之余短暂的避风港,是城市青年一种自我安慰、自我欺骗的人生和美学幻象。
“侘chà”“寂”美学的异化
在精神分析的研究中“,佛系”是一种时代的集体无意识心理,是一种被压抑的对象,在极端情况下会形成“负性幻觉(negative hallucination)”。英国学者 Christopher Bollas 在《精神分析与中国人的心理世界》中认为,正是对于眼中现实问题被转嫁的担心,激发了人们的“死亡本能”,种种“拒绝××”行动成了对抗被压抑的焦虑的象征性行动。“负性幻觉”表达为一种“无”,一种心灵死亡区域的积极呈现。然而,在对抗潜意识的破坏性方面,“负性幻觉”是没有作用的,因为这种“无”意味着自我或集体无法对付那种担心,而心灵已经废除了自己思考这种观念的能力。
正是面对现实困境时的“感觉身体被掏空”——一种无能为力的“丧气”感,佛教的“空”“无”等教义被征用为都市青年负性幻觉想象的理论工具。特别在东亚的发达经济体中“,佛系青年”奉行的“侘”“寂”美学近年来呈现日益流行的趋势,甚至影响到了欧美青年文化。乔布斯和苹果为代表的禅意设计美学大行其道便是例证。铃木大拙在《禅与日本文化》中认为,“侘”意味着真正的“贫困”,是“少欲知足”,是“不在时代的潮流中随波逐流”,在“文明化”的人工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现代人,希望回归内心深处,本能地憧憬与自然的生活状态想接近的原始的淳朴,而“寂”则代表超脱的“孤绝”。他们都或多或少带有消极的性质,这也是崇尚空无的“侘”“寂”美学能够在“佛系青年”中引发共鸣的原因。
“侘”“寂”美学的消极特征是城市孤独感的衍生物。孤独一直是病理学的研究对象。心理学家韦斯将孤独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是情感的隔绝,一个人与其他特定的个人没有感情上的联系;第二种是社会的隔绝,指一个人没有朋友或亲戚。在都市社会中,这两种类型的孤独总是一起出现。在他看来,孤独是“一种难 以根除的慢性病”。然而,孤独作为城市病也并非毫无 可取之处。一种“内在孤寂”往往成为艺术灵感的来源,如伍尔夫所说,这是一种真实世界在歌唱的感觉, 是一种可栖居的世界中孤独与静穆才能触发的感觉。这种感觉在禅宗中有时被称为“妙悟”,是一种“不将不迎”而又“反覆相明”的审美状态。它要求虚怀而物归, 认识到物物各具其性、各具其能“,因其所有而有之、因其所无而无之”,因此能不强加是非、不浮辩、不华辩,才能与万象各具其性的内在道枢同其节奏。
在都市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一种审美立场的“佛系”有其积极意义。它可以引导我们在纷乱而又孤独的社会中返归生命的诗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佛系青年文化”与“侘“”寂”美学只是形似而神不似“。佛系青年”是大时代中分裂的自我。虽然欣赏“侘”的自然淳朴状态,但并不能做到诗人式的“真正的贫困”。看上去有些凄凉,但只是时代潮流中的随波逐流,不能走进真正的沉思。有自我放逐的意愿,但只是“懒者”(并非是真正的弱者)的自我保护,如周志强教授所说,他们是一群“妈宝”,此类“小确丧”并不是超脱的“孤绝”,无法走向美学与道德、精神性的融合。
任何宗教都具有退化的特质,这是经历了孤立,经历了与世界的异化阶段,最终超越异化达到新的与“原初”合一。“佛系青年”也希望退回到自我,并谋求孤立,事实却是消费社会的“选择综合症”,始终停留在生命的异化阶段。如列斐伏尔在谈到消费社会异化时指出,异化就是这样扩展到全部生活,任何个人都无法摆脱这种异化。当他力图摆脱这种异化的时候,他就自我孤立起来,这正是异化的尖锐形式。
消费社会欲望机器的生产
“佛系青年”本质是消费社会异化统治下的“负性幻觉”。鲍德里亚曾经有个精妙的譬喻。他把关于厌恶、排斥、冷血、拒绝的文化比喻为“厌食症患者的文化”。这是一种肥胖、饱和、过剩阶段的特征,是一种深度的自恋人格。
节食、慢跑、佛系青年、性冷淡风、禁欲系、丧文化正是这种“厌食症患者的文化”的表现。这样一群被城市社交生活遗弃的人,陷入一种自恋的幻觉中,一种疯癫的自我指涉之中。“佛系青年”与慢跑者正在成为都市时尚,后者是将体内餍足的能量呕吐出来,前者则是将过量的食物、社交、情感、欲望纷纷呕吐出来。如鲍德里亚所说,这会导致一种新的形式的自愿奴役,成千上万个孤独的城市人,每个人都为自己奔跑,从不为别人着想。通过疲劳后的沉醉状态,一种机械性灭绝后的反常状态,都市青年试图达到“佛系” 对“空”的幻象——空虚的身体的沉醉。
鲍德里亚惊世骇俗地将慢跑比喻为一种新形式的通奸,因为此类“厌食症患者的文化”传承了历史遗产,那是三世纪基督教苦行者在匮乏和骄傲的静止中所寻求的东西,如今,苦修利用装有铬合金滑轮和可怕医疗假肢的复杂机器,实现了人与机器的欲望通奸。同样是2017 年,一方面是“佛系青年”的风行,另一方面却是“维密秀”首次登陆中国受到热捧。两相对照才能理解欲望生产的隐秘机制。消费的机器已经充斥在城市每一个角落。生产的丰富性里面故意筹划出需求,所有欲望在中间躁动不安,人们不得不听命于欲望,而一种对于难以满足之需求的巨大恐惧,诱发自我退隐和逃避的冲动,制造了“佛系青年”。
德勒兹和加塔利《反俄狄浦斯·欲望机器》中设想这样的终极场景:不再有人,也不再有自然,只有彼此之中生产的、把种种机器进行耦合的进程。到处是各种生产机器或者各种欲望机器、各种精神分裂症机器乃至无器官身体。我与非我、外部与内部不再具有任何意义。欲望机器集合了表面的强烈欲望与深处的无意义,正如“维密天使”与“佛系青年”交合的幻景。
“佛系青年”的自我孤立,有一种欲望间同类事物的互相联通,就像颓丧的“佛系青年”与积极的“慢跑者”其实也是一回事。
幻觉从来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幻觉”“。佛系青年”对于欲望的抵抗,其实是对于匮乏的反面确认,因为匮乏正是欲望的反效果。把匮乏组织到丰富的生产之中,使全部欲望转向匮乏的巨大恐惧中,最终现实的消费生产才可能成为唯一的依赖,而真正积极性的幻觉(譬如宗教、文学、艺术等)却从此进入了幻想之中,不再具有拯救意义。这正是消费主义所制造的终极的“负性幻觉”,也是唯物主义精神病学揭示的问题症结。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禅宗的美学是一种生命的诗境。“侘”是立,“寂”为住,真“佛系”是虽不自由却无不自由之念,虽不富足却无不富足之念,虽不完美却无不完美之念。而西方的虚无主义者尼采也教导我们: 就算人生是个梦,我们也要有滋有味地做这个梦,不要失掉梦的情致和乐趣;就算人生是幕悲剧,我们也要有声有色地演这幕悲剧,不要失掉悲剧的壮丽和快慰。这两段箴言对于深陷“负性幻觉”的“佛系青年”来说,不无拯救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