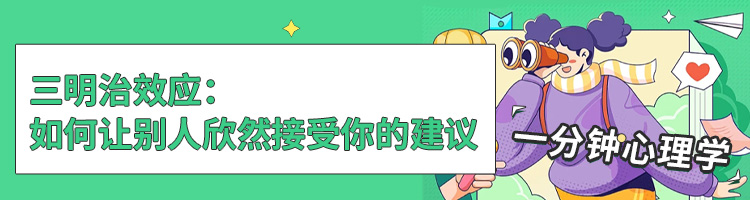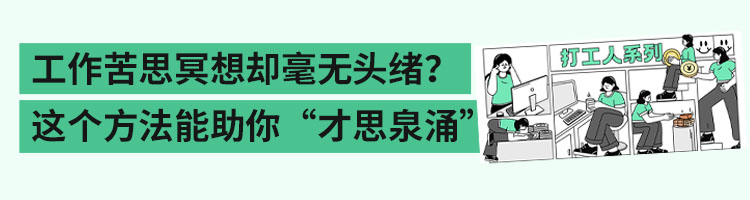我们如何在纸媒和数字媒体之间获得阅读能力
如果我们只是快速扫过浏览文本,我们就没有时间理解他人的感受、文本的复杂,也无法感知文本之美。我们需要培养一种新型的大脑:一种“双文化”阅读型的大脑,它能够在数字媒体或传统媒体上进行最深层次的思考。
我们需要培养一种新的大脑
一种“双文化”阅读的大脑
想象一下飞机上的情景。iPad是婴幼儿的新奶嘴。刚入学的儿童通过智能手机阅读故事;年龄较大的男孩根本不阅读,他们喜欢玩电子游戏。父母和其他乘客在Kindle上阅读,或者浏览电子邮件和新闻稿件。
我们大多数人都未意识到,阅读的游戏规则已经发生了变化,并且把每个人都绑在了一起:大脑阅读能力的神经回路正在微妙和迅速的变化着,这种变化对每个人都有影响,无论是孩子还是成人。
神经科学家认为,想要获得阅读能力,即便是6000多年前的人类祖先,也需要在大脑中形成一个回路。这个回路的演化始于对的基本信息的简单解码。例如,从羊群的数量,发展到现在高度精细的大脑阅读。
我的研究描述了我们的阅读脑是如何促进了我们一些最重要的智力情感发展过程:内化知识、类比推理和推理;透视取景;共情;批判性分析和洞察力的产生。
当今世界的很多研究警告世人,当我们进入数字化阅读时代后,这些基本的“深度阅读”过程可能受到威胁。
这不是简单的在印刷版本和数字阅读创新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Sherry Turkle所认为的,当我们创新时,我们不会犯错误,但是,当我们忽视了创新造成的破坏时,错误就会发生。
在印刷和数字文化之间选择的这个关键时刻,社会需要正视阅读导致的脑回路逐渐萎缩的情况,同样也需要重视孩子和学生还没有发展好的东西,并且关注我们能够对此做些什么。
我们从研究中知道,人类无法简单的通过视觉或语言等基因蓝图形成阅读回路,阅读脑回路的发展仰赖于阅读的环境。此外,脑回路也会适应环境的要求,这些环境包括不同的书写系统,以及所使用介质的特性。如果占主导地位的媒体加工过程是快速、多任务导向的(例如当前非常适合大量的信息的数字媒体),那么阅读回路也会变得快速,注意力也会分散。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心理学家Patricia Greenfield写道,其结果是,像推理、批判分析和共情这些需要较慢阅读速度的深度阅读,获得注意力会变少,阅读时间也会变得更少。而这些深度阅读的能力是任何年龄的学习不可缺少的。
屏幕阅读的负面影响最早出现在四年级和五年级
教育工作者和心理学和人文科学学者的研究报告越来越多地证实了这一现状。英国文学学者、教师Mark Edmundson描述了大学生因为不再耐心阅读更长、更密集、更难的课文而积极地避开19世纪和20世纪的经典文学,这一现象非常普遍。然而,我们与其关注学生的“认知急躁”,不如关注其背后的原因:
很多学生可能无法通过批判性的分析阅读发现并理解更高要求文本的思想和论点复杂性,无论是在大学文学和科学文本之中,还是在合同和故意混淆的公民投票之中,他们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阅读纸制书籍的学生在理解能力上优于屏幕阅读的同龄人,尤其体现在按时间顺序排列细节的能力和重构情节的能力上。
多项研究显示,数字屏幕的使用可能对高中生和大学生的阅读理解造成各种令人不安的影响。挪威Stavanger的心理学家Anne Mangen和她的同事研究了不同阅读媒介如何让高中生对同一份阅读材料产生了不同的理解。
Mangen的小组向每一位被试询问了与一篇短篇小说有关的问题,短篇小说的情节对学生具有普遍的吸引力(一个充满欲望的爱情故事);一半的学生在Kindle上阅读,另一半阅读的是平装书。结果表明,阅读纸制书籍的学生在理解能力上优于屏幕阅读的同龄人,尤其体现在按时间顺序排列细节的能力和重构情节的能力上。
圣何塞州立大学的刘自明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他发现,人们的阅读“新范式”是跳读、定点阅读和扫读文本。
现在,许多读者的阅读模式是先对第一行进行采样,然后对文本其余部分的单词进行定点分析。当阅读脑这样滑动时,减少了分配给深度阅读过程的时间。换句话说,我们没有时间去理解文本的复杂性,没有时间理解别人的感受,无法感知美,更不能创造读者自己的想法。
多项研究表明,使用数字屏幕,可能会导致阅读能力的下降。
Karin Littau和Andrew Piper注意到了另一个维度:身体性。
Piper、Littau和Anne Mangen的研究小组强调,摸着印刷品的阅读触觉感受增加了信息的重要冗余感——那是文字的“几何”,文本的空间“几何”。
正如Piper指出的,人类需要知道自己在时空中的位置,时空中的位置允许他们回到事物之中,并通过重新审视获得学习——他称之为“重现技术”。
对于年轻读者和老年读者来说,重复阅读的重要性在于能够追溯、检查和评估自己对文本的理解。那么,问题是,我们的年轻人在浏览屏幕时,屏幕阻碍了他们“翻到前面一页”的空间感,空间感的缺乏会怎样影响他们的理解力?他们的理解力又是如何变化的呢?
美国媒体研究人员 Lisa Guernsey和 Michael Levine,大学语言学家Naomi Baron,以及来自海法大学的认知科学家Tami Katzir研究了不同信息媒体对阅读的影响,尤其是对年轻人的影响。Katzir的研究发现,屏幕阅读的负面影响早在四五年级就显现出来,这不仅影响了理解能力,而且影响了共情能力的发展。
我们需要培养一种新的大脑
数字媒体可能对我们的批判性分析、共情和其他深层阅读过程造成的无意“附带损害”。这些损害并不是在印刷体和数字阅读之间进行非此即彼选择的简单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才能在任何媒介上阅读,如何同时改变我们阅读的内容和目的。而且,这个问题不仅仅和年轻人有关。
批判性分析和共情能力的微妙萎缩影响着我们所有的人。它影响了我们在信息爆炸的海洋中航行的能力。它刺激我们撤退到最熟悉的、未经检查的信息仓库,这些信息不需要分析,让我们更容易接收到虚假的信息,并被其蛊惑。
神经科学中有一个古老的规则
它不会随着年龄而改变:用进废退
ISTCOKFIX 卫报
将这一规则应用于阅读脑的批判思考之中是非常有希望的,因为这意味着选择。让阅读脑发生改变的故事不是一天可以完成的。我们拥有的科学和技术能够让我们在阅读方式的变化变得根深蒂固之前,识别并纠正这些变化。如果我们努力精确地理解我们将会失去什么,以及数字世界带给我们的非凡的新能力,那么,就如同兴奋一样,我们有理由更加谨慎。
我们需要培养一种新型的大脑:一种“双文化”阅读型的大脑,它能够在数字媒体或传统媒体上进行最深层次的思考。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o 公民在充满活力的民主中尝试其他观点的能力、辨别真相的能力;
o 我们的子辈和孙辈欣赏和创造美丽的能力;
o 以及我们超越目前信息过剩的能力,以达到维持良好社会所必需的知识和智慧。